近日,一則關于“換頭術”的新聞吸引了公眾眼球,引發熱議。意大利神經外科專家賽吉爾 卡納維羅醫生宣布,將與中國醫生任曉平團隊合作,計劃于2017年12月在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進行世界首例“頭顱移植手術”。對此,《生命時報》記者采訪了任曉平本人,并邀請國內神經外科、倫理學及移植專家答疑解惑。
中國當事醫生:手術面臨三大難題
意大利醫生賽吉爾 卡納維羅是新世紀以來在“換頭術”領域最活躍人物之一,而哈爾濱醫科大學手顯微外科中心主任任曉平教授研究該課題也有多年。上世紀90年代,任曉平就在美國路易斯維爾大學與團隊一起完成了人類首例手部移植手術。2013年,他和團隊完成了首例小白鼠頭部移植手術,隨后對約1000例小白鼠展開了類似手術,術后小鼠們能睜眼、呼吸以及完成一些其他基本動作。卡納維羅在看到任曉平的文章后,了解到彼此研究領域很符合,因此決定開展合作。目前,準備接受手術的志愿者是30歲的俄羅斯計算機工程師斯皮里多諾夫,他患有先天性脊髓性肌肉萎縮癥。
“換頭術”指的是將“腦死亡但其他部位健康”的身體,捐獻給腦部健康但肢體功能缺乏的患者。任曉平告訴記者,這一通俗說法沿用了傳統的“器官移植”,但他也一直認為不夠科學,用“異體頭身重建術”的命名更嚴謹,也能降低手術話題的敏感性。
盡管在之前一系列實驗和手術中已積累了相對豐富的經驗,但任曉平也承認,這一課題尚有許多技術難題有待攻克。首先要解決的是缺血器官的損傷。在傳統的器官移植中,器官可存活幾個小時,醫生能在有效時間內盡快完成手術。但頭部在室溫情況下超過4分鐘,就會造成不可逆的損傷,即使手術完成,腦細胞也可能已經壞死。第二個難點是免疫排斥反應,目前尚不清楚現有的聯合免疫治療方案是否能有效適用于該手術。第三個難點是中樞神經的再生和功能恢復。傳統醫學認為中樞神經不能恢復,但醫學發展也為該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很多實例。此外,研究人員也試圖從其他角度解決,比如利用外力在中樞神經無法恢復的情況下,幫助病人站起來。
專家質疑:神經無法再生,幾年內不可能
在任曉平提出的多項難題中,最后一點爭議和關注最多。北京市神經外科研究所副所長吳中學教授告訴《生命時報》記者:人體中樞神經系統內有億萬個神經元,其中的聯系十分復雜。簡單來說,中樞神經元的發展是人在成長過程中形成的,而換頭相當于將顱頸完全切斷,這會導致細胞間傳導中斷,形成潰退。換頭需要重新連接,讓細胞再生。在目前的醫學水平下,被切斷的神經元不會再生,即使再生也不再具備使用功能,無法完成對肢體的控制。不僅如此,中樞神經系統對身體的支配分很多級別,想要解決這一難題,必須逐一攻克,這在短短幾年內不可能實現,要100年甚至更久。
吳中學告訴記者:人類在對自身的醫學探究中,對腦部的認識尚屬“年輕”,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現階段,無論從科學還是倫理層面講,該手術都是很荒謬的。
人體移植難度很大,以“腎移植”為例,解放軍第309醫院全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教授告訴《生命時報》記者:“從1960年我國實行第一例人體腎移植,到1972年我國成功實施了我國第一例親屬腎移植手術,歷時十幾年。”石炳毅強調,大腦不同于單個器官,不能進行簡單類比,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更多。
“我認為,就如同近期報道的女作家冷凍遺體,等待50年后‘復活’一樣,從科學本身出發,愿意進行嘗試,總歸是一種進步,”吳中學說,我們應該用理性的觀點看待,謹慎的態度去執行。任曉平也強調,“異體頭身重置術”是一項重大的前沿課題,關系中國在現代醫學中的地位,不應當成兒戲來炒作。即使存在爭議,科學家也不應該回避,未來任重而道遠。
倫理爭議多,專家呼吁要接受生死
目前,這一課題也引起人們倫理學方面的討論。俄羅斯“報紙報”網站援引瑞典著名移植外科醫生保羅的話說“這一手術是不可能的,在道德上也不可接受,是一種犯罪行為,沒有任何科學基礎,類似于超人。”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生物學副教授約瑟夫 鄧特則認為,盡管該話題備受爭議,但此類手術并不存在嚴重的倫理問題,從根本上說,它與心臟或肺移植手術沒有區別。
北京大學醫學部衛生法學教研室副主任王岳教授對《生命時報》記者表示:“拋開目前法律問題,從倫理學角度來說,我個人反對異體頭身重建術。退一萬步說,哪怕該手術成功,我們如何去界定這個人的身份,是捐獻者復活,還是像志愿者斯皮里多諾夫一樣的下肢受損者會動了?另外,人的生命不能僅用科學來解釋,還要從心理等人文角度考慮。大眾應接受生死,接受生命有長度,在戰勝疾病和生死恐懼的道路上,不能一味強調科學。人類可以沒有信仰,但萬萬不能沒有對生命與自然的敬畏之心。”▲(生命時報記者 范凌志 包育曉 實習生 吳雪翌)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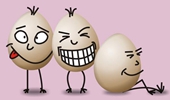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